爸爸活着的时候,妈妈最难对付的事就是为爸爸筹钱办学校。三四十年代,像父亲这种文化人,教育家,薪水较高,我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他记的收入到当月薪水800元,之外,他兼几所中小学的教务和讲课,收入不菲。他除了给妈妈一些钱带孩子以处,几乎从不留别的钱给妈妈。藉口只要一个:给学校了!盖教室,修通往学校的路,发教职人员的工资,发给学生奖学金,建学校图书馆,资助困难学生。他不停地工作,写文章投稿,当时,《大公报》在天津创立,《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民报》都相继创刊。爸爸每天都要为这些报刊写稿赚取稿费,目的是养家、办教育。父亲酷爱买书,十几年当中,他在家里建立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图书馆--《万有文库》、《东方文库》,他总是一买就两套,学校一套,自己留一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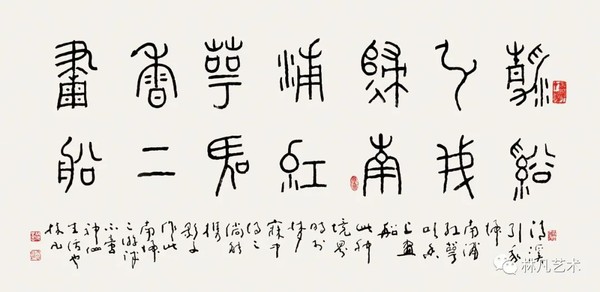 爸爸也偶然买些美术、书法的启蒙读物,比如《芥子园画谱》、《马骀画谱》。妈妈后来对朋友们说起爸爸,这种作法,是以一种埋怨而又自豪的口气。说:翊宇他爸有个莫名其妙的做法是要在我们的住处堆满各种书,让书包围孩子们,让孩子们四方八面都是书,抬头是书,低头是书,躺下是书,坐着是书,不让他们好好上学,买那么多书,也保不准孩子们数学不及格。
爸爸也偶然买些美术、书法的启蒙读物,比如《芥子园画谱》、《马骀画谱》。妈妈后来对朋友们说起爸爸,这种作法,是以一种埋怨而又自豪的口气。说:翊宇他爸有个莫名其妙的做法是要在我们的住处堆满各种书,让书包围孩子们,让孩子们四方八面都是书,抬头是书,低头是书,躺下是书,坐着是书,不让他们好好上学,买那么多书,也保不准孩子们数学不及格。

爸爸爱书如命,是从祖父那里传过来的。祖父是个书迷。我不知道从曾祖父三元公这个老农民是怎么转变成书迷的。打从我记事起,我家的书分两大部分,一是祖父的线装书;一是父亲的洋装书。妈妈是个半知识分子。她看得懂《水浒》《三国》《红楼梦》,外国小说也看得懂,就是看不懂祖父的那些古文辞类纂。祖父过世,妈妈就坚持把这一部分线装书全部寄存在亲戚家。我们亲戚当中唯一有田产的就是姨翁妈家,姨祖父周先梯是当地周姓的大户,房屋较宽敞,妈妈一交涉,姨翁妈马上答应,在她家偏屋,腾出一个谷仓,来装林家亲戚的书。我们是没有房产的读书人。妈妈就开始“大迁徙”,一年搬两三次,围绕清溪村就搬了近十处。搬家是一挑锅盆碗碟,吃饭的这一套,一挑是被子褥子,枕头和衣帽鞋袜。另一挑是雪君占一箩筐,其他杂物占一箩筐,剩下三、四挑全是爸爸的书。益阳流传的老话是“人搬穷,火搬灭”。几年下来,东西越来越少,衣服被褥补丁越来越多。生计再也没有翻过身来。由于妈妈的坚持,倒是总的方向是越来越靠近信义中学。即使父亲不在了,信义女中是爸爸创建的,无论如何说起“信义”这两个字总感到亲切,感到有靠头。但信义中学搬到安化躲日本鬼子这几年,东搬西挪,还结交了不少朋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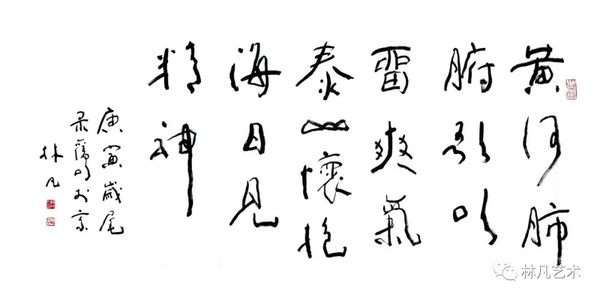
舅舅在世的时候,妈妈是以兄妹之谊,靠定了舅舅。舅舅过世,舅舅一家和大姨妈(益阳叫媠妈)一家就随着妈妈转,舅舅家有两位舅妈。高个子舅妈,矮个子舅妈,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第三位老太太有这么勤俭利索。当年舅舅家靠木料、楠竹发了家,一切都很讲究,蚊账是西式的,被子是套被,干净利落,邻居们十分羡慕。抗战几年下来,衣被虽然补丁多了,但仍然十分干净。加上舅娘的贤慧,亲友们仍然十分尊敬,十分热络。日本鬼子一来,舅舅去世,两位舅娘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后来大姨妈也搬过来,大家穷到一块,乐到一块,倒也自在。如果拿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亲友中,有两个像小企业家一样的小作坊老板,一个是大姨爹,他家做了十年毛巾生意,从整纱、买土纱、漂染,到按每个顾客的要求织成各种规格的毛巾,都是全家加上顾工一齐上马干。当年益阳男人,都喜欢像印度人一样缠上几十圈的长毛巾,缠在头上,越长越帅,越长越英俊。大姨妈家就专门做这种长毛巾生意。最热闹的当口,有十来架毛巾织机同时开工。另一个就是我的堂哥林尚熙织袜子卖,他挑着织袜机到乡村或摆渡上益阳、下益阳地跑生意。
这两家忙得正火的时候,日本鬼子侵占中国面积越来越大,顾了东,顾不了西,控制放松了,东西洋货进来,两家本地生计都垮了。1940年,日本人多次轰炸之后,侵入了益阳,也时常骚扰益阳近郊。妈妈把祖父的线装书寄放在清溪村以后,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带我们去姨翁妈翻晒这些老书。顺便看看姨翁妈,书摊在禾坪里,用晒谷的簟子衬着,上午十点钟左右,书翻晒了第一遍,公鸡打午鸣了,清溪村一切安详而沉静,突然,有人跑过来嚷道:“鬼子进溪口啦,快跑!”妈妈犹豫了一下,抱着雪君,催促我和两个大些的妹妹往对面山上跑。靠近屋场这边,大都是山茶,树矮小,藏不住人。刚走下山,鬼子就来了。一阵乱乎,鬼子让人把书堆起来,洒上汽油,枪一响,火突地腾起,书全完了!鬼子走了,妈妈到上屋探看姨翁妈,问安压惊。姨翁妈反倒说:淑芬,真对不住,你看蛮以为在清溪村能躲过这一劫,到底没躲过去。改天我得上印莲相公坟上烧张纸嗑个头告个罪,说着说着两人竟相拥着哭起来了。祖父的线装书全烧光了,只有我当时正在翻看的半部《阅微草堂笔记》扔在门后保存下来。
妈妈像犯了罪似的带着我们四人,到祖父坟上叩头告罪。从这以后就更加小心翼翼地照看父亲的书了。妈妈爸爸感情好,不消说:对祖父也是尽了孝心的。祖父刚中风时大小便失禁,一天要换十多套裤。吃的、喝的要人招呼,作为媳妇,她尽了最大的心力了!所以祖父弥留之际,对妈妈说:淑芬我这当公公的,什么也没有给你留下,对不住啦!我和伯陶把最重的担子都卸给你了,对不住啦!对不住啦!祖父很喜欢我,但也嫌我顽皮。不到五岁就送我上小学,叫老师到家里来叮嘱他说:“涤伢崽是猴子变的不打不成材,你放心管。”老师叫周复初是祖父的学生。由于祖父的叮嘱周老师竟在我学业不好又顽皮难管的时候,对我十分严厉。用戒尺打我手板就好几次。父亲过世的秋天,祖父也病重躺在躺椅上养神。我为了找个什么东西,竟爬到祖父头顶上的摆柜上去翻腾。摆柜上有我家最神圣的一件宝物是祖父当年跟鲍超在天津告别时鲍超请泥人给他自己和祖父各做了一尊小泥像,小泥像把祖父塑得惟妙惟肖,光头留着长辫子,潇洒而又矜持。祖父把这尊像带回益阳造成不小的轰动,说真是印莲相公的神!全家把这尊像看成是镇家之宝。这回搬家搬到陈家屋场,这尊像就放在堂屋的柜子上。祖父的躺椅就靠着柜子。当时,我八岁精力正旺,不知道找什么东西,在柜上正翻腾什么?恰好衣袖破了个大洞,破洞恰好套在祖父泥像的头。手一缩咕咚哗啦!把泥像带下来摔得粉碎。
祖父喝茶的宜兴壶也摔下来了祖父醒来了,妈妈从外屋听到响声跑进来,看着碎泥像一边发楞一边流泪。转过身揪着我耳朵拉到外屋一顿暴打。祖父剧烈地咳嗽,妈妈赶忙进去照应。祖父欠起身子说:淑芬别打了!我林文凤命该到底了,落凤坡的星星掉了,长不了啦!别打他了。妈妈“嗡…”了一声拿扫帚把泥像碎片和茶壶碎片打扫干净,拉上屋门走了。自打这事件以后,我的坏名声在亲友当中传遍了!我也自觉成了祖父的克星更抬不起头了。书烧光了,泥像没有了,过了不久祖父去世了。
祖父在家乡名声很好,但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一张两寸高的全家福的黑白小照片。传到前几年还在,祖父坐在当中。我靠在祖父身上,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围成一起,当时香港文汇报要整版报导我的书画成就,用上了这张照片。竟忘了要回来,想到这些心里格外难过。是我消灭了祖父的一切!连最后一张小照片也没有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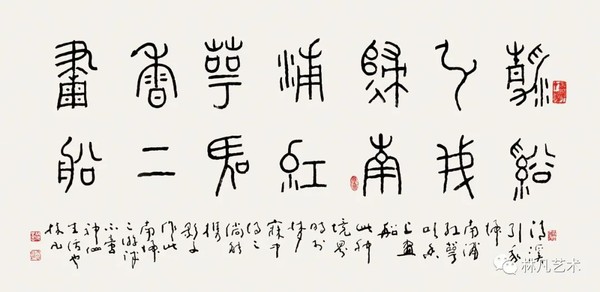 爸爸也偶然买些美术、书法的启蒙读物,比如《芥子园画谱》、《马骀画谱》。妈妈后来对朋友们说起爸爸,这种作法,是以一种埋怨而又自豪的口气。说:翊宇他爸有个莫名其妙的做法是要在我们的住处堆满各种书,让书包围孩子们,让孩子们四方八面都是书,抬头是书,低头是书,躺下是书,坐着是书,不让他们好好上学,买那么多书,也保不准孩子们数学不及格。
爸爸也偶然买些美术、书法的启蒙读物,比如《芥子园画谱》、《马骀画谱》。妈妈后来对朋友们说起爸爸,这种作法,是以一种埋怨而又自豪的口气。说:翊宇他爸有个莫名其妙的做法是要在我们的住处堆满各种书,让书包围孩子们,让孩子们四方八面都是书,抬头是书,低头是书,躺下是书,坐着是书,不让他们好好上学,买那么多书,也保不准孩子们数学不及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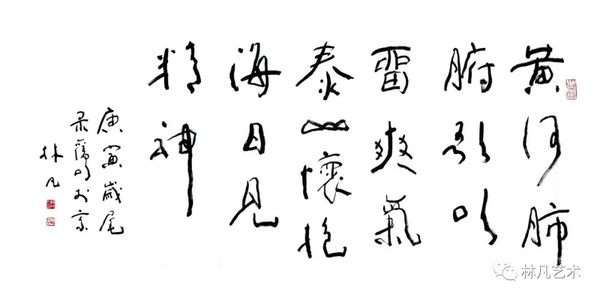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0792号粤ICP备17056390号-4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909402号互联网域名注册证书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0792号粤ICP备17056390号-4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909402号互联网域名注册证书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